一个造假者,却要在三天内拯救另一份“辛德勒的名单”
时间:2020-01-08 12:48:32 热度:37.1℃ 作者:网络
未读 文学报
隐身大师

“我多睡1小时,就有30人丧命!”一场堪比《辛德勒的名单》的惊心动魄的拯救故事,也是一段真实的口述历史。
主人公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二战”期间,染匠学徒出身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纳粹的魔爪。
今日夜读,进入历史的隐秘,重温生命之光。
01
我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巴黎的伪造者。我还知道这是因为我找到了大规模伪造证件的方式,这些证件早就遍布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荷兰。我最大的优势在于,警察们可能一直都在找一个拥有机器的“专业人士”,有印刷机和木浆厂。他们肯定不会猜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伪造者,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

19岁的卡明斯基
很明显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实验室的头儿叫萨姆 · 库杰尔,二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水獭”。上一个负责人是勒妮 · 格卢克,同样二十四岁,代号“睡莲”,是一名药剂师,后来离开这里去护送孩子们和处理边境前线事宜了。实验室的成员还有在艺术学院就读的苏西 · 席德洛夫和赫塔 · 席德洛夫姐妹俩,她们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凭借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减的幽默感为实验室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就是传说中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神秘分支“第六部”伪造证件实验室的人员配置。

卡明斯基团队当年制作的一些伪证
我们假装成画家作为掩护。伪造证件的实验室在圣佩雷斯街十七号的一间狭窄的顶层小阁楼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艺术工作室。我们会在旁边放上几支画笔,好让人以为这些瓶瓶罐罐都是绘画用的颜料和溶剂。为了升高工作台,我在两张桌子底下胡乱拼凑了数十个抽屉架。
这样,我们就能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一次性晾干大量证件了。还有几面墙上挂满了我们匆忙完成的画作,在这些画的背面藏着我们伪造好的证件,直到能把它们交给联络人。

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日程表和办公时间,以免引起看门人的怀疑,而且时不时地,我们还会带着画家专用的调色板过来。所以,没有一个邻居过来问我们屋里为什么会有化学品的气味。查电表的人也是如此,每次他进来都会恭喜我们完成了新的画作。当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时,我们总会爆发出一阵大笑。要知道那些都是乱画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02
我们为所有人服务。订单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数量越来越大。其中有来自巴黎的、来自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来自南部地区的,还有来自伦敦的。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工作节奏来应对这几近无法控制的工作量,有时甚至一个星期要做五百个证件。一般情况下,由水獭和我负责联络那些下订单的人。

我记得水獭看上去也很天真无邪,和我一样。这是我们最好的伪装。通常,我们会把见面地点安排在巴黎一些繁华的地段,最好是和一个女人接头,这样见面时就可以假装是正在约会的情侣。一旦感觉被监视了,两人就会深情地对视。当我们分开时,彼此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但有一次和我见面的不是我虚拟恋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马克 · 哈蒙,绰号“企鹅”,他也是法国犹太童子军的一员,当初就是他把我招进了抵抗组织。我明白,如果是企鹅亲自来的话,那就说明问题非常紧急,他已经等不及让组织里有空的女成员来了。
“昨天伦敦电台给我们传来了一些好消息。德国军队正在全线撤退,而且从现在起,所有北非军队都站在我们这边。不过问题是,纳粹决定加速清除犹太人,正准备在整个占领区内实行一次大型围捕。三天之后,巴黎的十个儿童福利站将会同时遭到突袭。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清单。我需要上面的一切材料:定量供应卡、出生证明、洗礼证明,还有协助孩子穿越前线的大人的身份证、命令单,以及所有人的通行证。”
“有多少?”
“你是说多少个孩子?……超过三百个。”
三百个孩子。这意味着要准备超过九百个不同类型的证件,而且是在三天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一般来讲,每天收到的订单数量有三十到五十个,有时候会多点。此前我也面临过巨大的挑战,但这一次数量实在太过巨大,我震惊了。

和企鹅的会面结束之后,我第一次害怕起失败来。在这之前,我总能通过积累的各种知识,想出一些神奇的办法来解决技术问题。但这一次我们要的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巨大的数量,而我清楚当时自己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
一天的时间不会缩短,但不幸的是,它也不会延长。没时间多想,我得先去雅克布路造纸:紧致的、好用的、密实的或精细的,有纹理或没纹理的——根据证件原本的质地来准备。我必须得抓紧,倒计时已经开始,比赛的枪声已经打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与死亡的抗争。
03
我抱着装满空白证件的公文包气喘吁吁地赶到实验室时,水獭、苏西和赫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令我惊讶的是睡莲也在——因为有别的任务,最近很少能在实验室看到她。他们都看向我,表情无比震惊。他们告诉我说已经接到了通知,毕竟事关三百个孩子——这也是睡莲会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她是特地来帮我们的。
除此之外,水獭还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移民工人组织的订单:他们需要给匈牙利小组的成员准备证件。所有人都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他们想知道:我们真的能满足所有需求吗?为配合当前这种紧急的情况,我把一个装满空白证件的纸箱子放在桌子上,用行动给出了一个信号。
“孩子优先!”睡莲补充道。
实验室里马上变得一片忙碌:睡莲负责用切纸机把纸板裁成卡片,苏西填色,赫塔用笔和打字机填写文字。只有水獭,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参与制作,只负责管理所有行政琐事,像游魂一样转来转去,茫然无措。
“如果你想帮忙,那就从盖章和签字开始吧。”
于是他立刻投入工作。而我正用一台自己造的机器把纸张做旧:塞进去一些灰尘和铅笔芯,然后转动把手,让纸张看起来又脏又旧,以免看上去太新,或者像是刚从打印机里拿出来的一样。屋子里慢慢开始弥漫起一种化学用品混合着汗水的气味。在不同的角落里,我们切纸、裁边、盖章、上色、打字,在这个简易文书工厂里埋头苦干。

我们把做好的假证件放到镜子背面和底部可拆卸的抽屉里,塞得满满当当。虽然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完成,但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把它说出来。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毕竟,除了乐观,我们一无所有,这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
天黑以后,所有人都回家了,我朝位于雅克布路的实验室走去。即便有睡莲和水獭的帮助,我们一整天也才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睡觉?按照这个节奏,我们或许能完成孩子们的证件,却要以牺牲那些匈牙利人为代价。这让我无法接受。保持清醒,时间越长越好,和睡眠做斗争。算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小时我能做三十张空白证件;如果这一个小时我用来睡觉,就会有三十个人因此而死去……
04
经过两个晚上无止境的痛苦工作,我的眼睛几乎快要贴到显微镜上——疲劳成了我最大的敌人。我得一直屏住呼吸,伪造证件是一项只有一丝不苟才能完成的任务——你的手甚至不能有一点抖动,是非常精细的工作。哪怕一瞬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会是致命的,因为每一张证件都生死攸关。
每一页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哪怕它们已经很完美了,我还是会担忧。那就再检查一遍。压力虽然消失,但更糟的是,我已经在打盹儿了。我站起来想让自己精神一下,在屋里走了几步,甚至扇了自己几巴掌,然后重新坐下。
一个小时等于三十条人命!我没资格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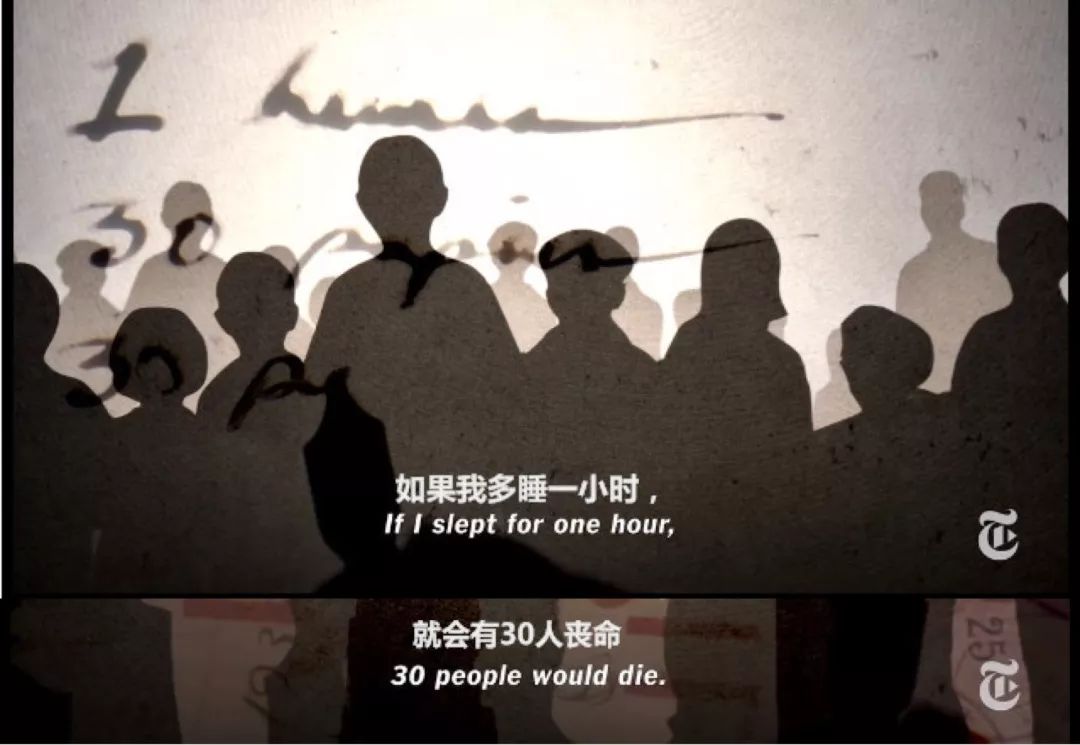
我眨了眨眼,然后眯起眼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到底是我把这些东西印模糊了,还是我的眼睛在这暗室的微弱灯光下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三天,圣佩雷斯街的实验室里充盈着一股激动的情绪。
我们就要完成任务了。下午五点,水獭和睡莲就会带着我们做好的所有证件出发,这是我们三天来不眠不休劳作的成果。当我们这天早上已经完成八百多份证件的时候,我终于开始有信心了。

所有人都像机器人一样,疯狂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们以熟练的手法不停歇地工作,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我们的衣服早已变得油腻,散发着化学品的刺鼻味道,身上全是汗,不过这一天空气中却散发着一种新的气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飘在空中。那是狂喜!我们大声地喊出一个个数字来为自己鼓劲:八百一十、八百一十一、八百一十二……
伴随着打字机不间断且有节奏的嗒嗒声、切纸机的撞击声、盖章的砰砰声、订书机的咔嗒声,还有纸张做旧机器低沉的隆隆声。
正当我沉醉于各种操作的旋涡中时,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在那一瞬间彻底晕了过去。我眨了眨眼,又眯了眯眼睛,但无济于事。感觉眼皮很沉,没有知觉,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听觉被一阵持续的嗡嗡声所取代,双手麻木。感觉身体一下子不再受自己的控制。我再也无法支撑自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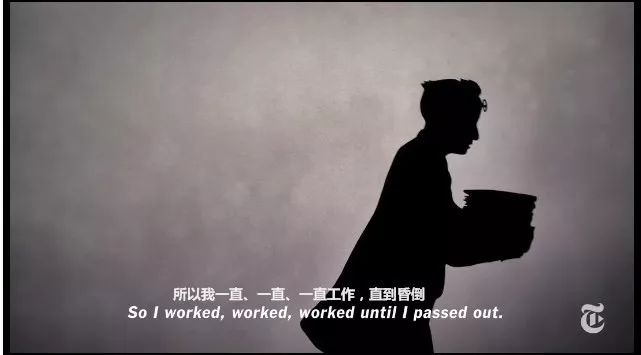
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蒙着眼罩。睡莲把我带到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联络员的家里,以便有人照顾我。我很担心会因为自己不在而导致证件无法及时完工,坚持要他们别让我睡超过一个小时。我还记得睡莲当时说的话,这句话把一种对他人生命的责任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证件伪造者阿道夫,而不是另一具尸体。”
本文选自

作者: [法] 萨拉•卡明斯基
出版社: 未读·文艺家·北京燕山出版社
译者: 廖晓玮
出版年: 2019-11
图片来自于CBS纪录片《隐身大师》
新媒体编辑:袁欢
原标题:《一个造假者,却要在三天内拯救另一份“辛德勒的名单” | 此刻夜读》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