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Deepseek:1B期非小细胞肺癌到底该先靶向治疗还是先随访有复发转移再治疗?
时间:2025-02-25 12:09:36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前言:前些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争论,合并存在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到底术后即予以辅助TKI治疗,还是先随访等出现转移后再予以TKI治疗?后来由于有些研究认为早用比晚用好,所以先用的占了上风,特别是ADAURA研究的重磅发布,直接改写了肺癌诊疗指南,1B期以后分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存在EGFR突变的术后辅助靶向治疗成了标准。但当时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入组该研究的部分分期是按第七版的TNM分期的较早的病例,或许缺乏细致分层的推荐会导致部分病例的隐形过度治疗。对于本身中晚期的,由于本来治疗效果欠佳,也不必太考虑TKI使用导致长久可能的副作用。而若对于相对早期的1B期,如果按我们之前的意见与理念,部分是“真早期”的病人,不加区分的只要1B就予以靶向治疗是否会存在事实上的过度治疗?靶向药导致的长期副作用或对机体的影响如何?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天我们问问Deepseek,看看它是如何看待1B期先靶向还是先随访的问题的?
问题:
1B期非小细胞肺癌伴EGFR突变时,先靶向治疗后观察随访与先观察随访发现转移后再靶向治疗,效果有何区别?
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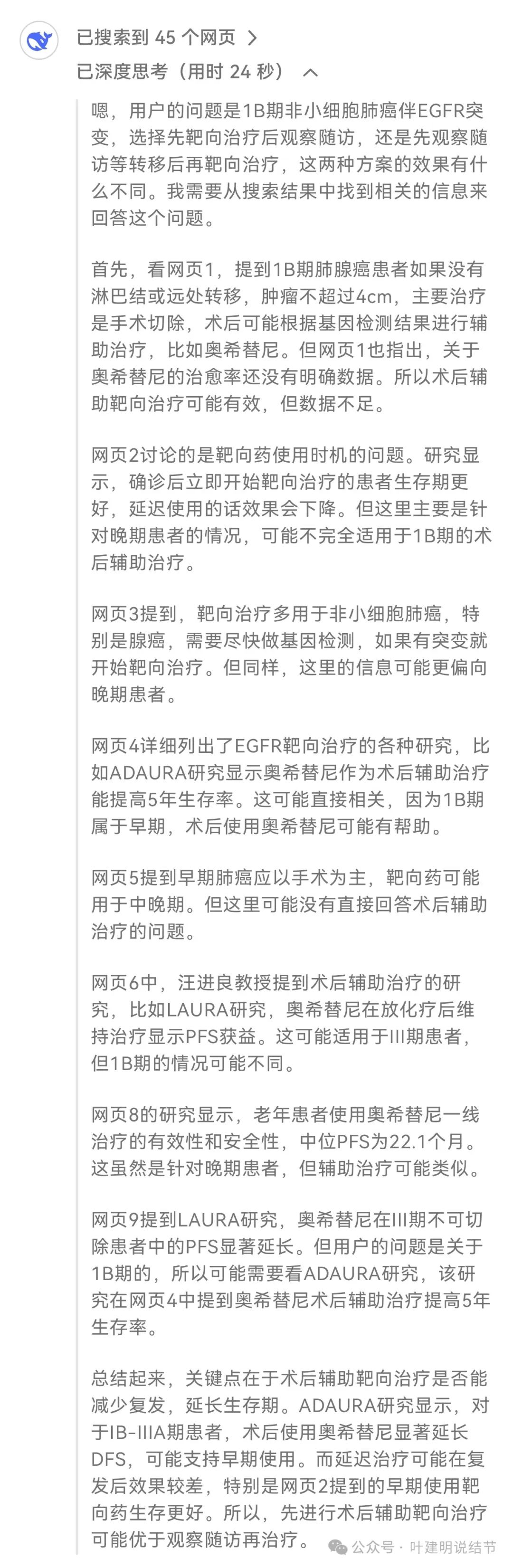
回答:
对于1B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伴EGFR突变的患者,选择“术后立即使用靶向治疗”还是“观察随访、复发后再使用靶向治疗”,其效果差异主要体现在复发风险控制、生存获益及耐药性管理等方面。以下是综合分析:
1. 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临床依据
(1)降低复发风险:
根据ADAURA研究(网页4、网页9),术后辅助使用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可显著延长无病生存期(DFS)。例如,在IB-IIIA期患者中,奥希替尼组的中位DFS未达到(对照组为19.6个月),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了83%。尽管该研究未单独分析IB期亚组,但整体趋势支持早期靶向干预的获益。
(2)脑转移控制:
奥希替尼具有较好的血脑屏障穿透能力,术后辅助治疗可降低脑转移发生率。研究显示,奥希替尼组的脑转移进展风险显著低于对照组(HR=0.18)。
叶建明的想法:在ADAURA研究中,正是由于未单独分析IB期亚组,把此分期中的那些低风险的(叶建明所谓的“真早期”的病例)放到了整体相对较晚(叶建明所谓“伪早期”的病例)的群体中去,从而导致结果可能产生偏倚,所以也就在整体趋势中支持早期靶向干预的获益。就如此前我质疑缺乏分层的那篇微信文章中说的,第7版分期中的实性,4-5厘米的肺癌,即使淋巴结阴性被分到1B期,也是风险较高,很可能是“伪早期”的,而混合磨玻璃结节因为靠近胸膜从而侵犯了胸膜(若更是未侵透,只是侵及),才分到1B期,从风险角度来考虑,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没有更细致的分层,这类病人(或许入组时极少有这类病人,因为磨玻璃密度肺癌是最近这十几年才大量检出的)只因为分到1B期,结果被靶向治疗,显然很可能存在过度治疗。那其实是用传统肺癌分期(实性病灶为主)套在新出现的肺癌(磨玻璃密度肺癌)上导致的偏倚,就如前些年,原位癌、微浸润性腺癌做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都是最为符合指南精神、最正确的一样,却在事实上成了“合规的过度治疗”!AI分析中还提到脑转移的控制,关键问题仍是1B期的脑转移的概率高吗?分层后的低风险的,很可能是“真早期”的1B期的群体呢?若本来就不会脑转移,谈可控制?
2. 观察随访后治疗的局限性
(1)复发后再治疗的生存获益有限:
多项研究(如网页2、网页6)表明,延迟使用靶向药可能降低生存获益。例如,回顾性分析显示,确诊后1个月内开始靶向治疗的患者生存期显著优于延迟治疗者,且随着时间推移,获益程度逐渐下降。
耐药机制复杂化:
若术后未接受辅助治疗,复发时肿瘤可能已产生更多基因异质性或耐药突变(如T790M、MET扩增等),此时靶向药的有效率可能降低。例如,三代TKI奥希替尼对T790M突变的耐药患者有效率仅约70%,且后续耐药后治疗选择更有限。
叶建明的想法:没有治疗肿瘤自己就耐药了?确诊后早开始靶向治疗的研究是否只是在晚期肺癌中显示早用早好的效果?因为术后辅助治疗没有可评价的指标,尤其是我说的1B期的话。
3. 两类策略的潜在风险与争议
(1)过度治疗风险:
并非所有IB期患者术后均会复发(约30%-50%的IB期患者可能长期无病生存)。过早使用靶向药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药物暴露和副作用(如皮疹、腹泻等),尤其是老年患者需权衡耐受性。
(2)耐药管理:
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可能加速耐药突变出现,但临床数据显示,三代TKI(如奥希替尼)的耐药时间较长(中位PFS约18.9个月),且耐药后仍可通过联合化疗或新型药物(如ADC、双抗)延长生存。
叶建明的想法:真正的问题就是对于“真早期”的患者过度使用了本该对“伪早期”起作用的靶向药,这必然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这类病人本来就是能长期生存,靶向药使用3年到底会对原本已经是正常的机体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会不会引起基因或微观层的其他问题;二是药物的过度使用没有获益却必会导致耐药株的产生。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不断的将适应证前移需要考虑必要性与长期影响。
4. 指南与临床实践建议
(1)指南推荐:
目前NCCN和CSCO指南推荐,对于IB期高危患者(如肿瘤≥4cm、分化差、脉管侵犯等),术后可考虑辅助靶向治疗。若无高危因素,则倾向于观察随访。
(2)个体化选择:
需结合患者基因突变类型(如19del vs. L858R)、合并症、年龄及治疗意愿综合决策。例如,老年患者(≥75岁)使用奥希替尼的安全性良好,中位PFS可达22.1个月。
叶建明的想法:如何从目前可及的临床与病理资料来区分“真早期”与“伪早期”,这才是选择有针对性、有分层的1B期肺癌是否靶向治疗的关键。相对来说,高危亚型、高危因素、随访进展较快、年纪较大(因为预期寿命不太长,靶向药长期影响相对就少)、术前影像密度与实性占比等是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
总结
优先推荐术后辅助靶向治疗:
对于高危IB期患者,早期使用奥希替尼可显著降低复发风险并延长生存期,尤其是合并脑转移风险较高的人群。
观察随访的适用场景:
低危患者(如肿瘤小、无高危病理特征)可暂缓靶向治疗,通过密切随访(每3-6个月影像学检查)监测复发,必要时再启动靶向治疗。
未来需更多针对IB期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以明确辅助靶向治疗的最佳人群和时机。

再问:
叶建明认为,随着近些年磨玻璃结节发现的增多,大量混合磨玻璃结节被手术,其中靠近胸膜的容易侵及胸膜,那么他们都是ⅠB期的,磨玻璃结节或混合磨玻璃结节的侵犯胸膜与实性肿瘤长到3-5厘米或侵及主支气管但未累及隆突或伴阻塞性肺炎或肺不张的实性肿瘤预后是不是一样?是不是有同样的恶性生物学行为?而且指南中说,当时入组的ⅠB期是第七版分期中的ⅠB期,而且给出了第7版与第8版的对比,如下图所示:对于ⅠB期以后的,予以术后辅助治疗,包括TKI治疗,我觉得都毫无异议。主要是ⅠB期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单独再列出来看看:这其中对于第7版中的前3条,肿瘤3-5厘米或累及主支气管距隆突大于2厘米(图中漏了“主支气管”这几个字),或者肺不张阻塞性肺炎未及全肺,那无疑值得辅助靶向治疗的。但纠结的是其中的侵犯脏层胸膜这一条,若肿瘤3厘米以下,或仅2厘米左右的纯磨玻璃结节或混合磨玻璃结节,只是因为靠近胸膜从而有累及。而这种情况在目前磨玻璃结节是手术后最主要类型的情况下,是很常见的!这么多不同的情况是ⅠB期,如果没有分层,没有统计只针对磨玻璃结节的,或者小于2厘米,或1厘米的,但靠肺表面较近,以致脏层胸膜受累,这部分病人的数据也支持术后辅助靶向治疗,那么可能对这些病人按指南予以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就存在过度治疗(也是符合指南但事实上过于积极)。叶建明的观点是否更从临床实际出发,确实要有更细致的分层推荐才更合理?
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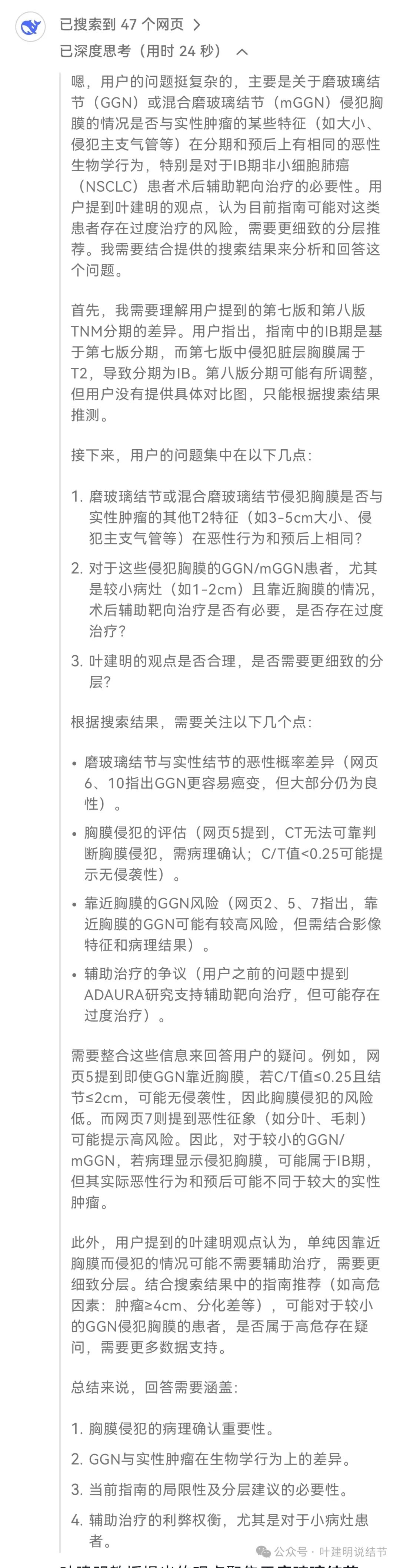
回答:
叶建明教授提出的观点聚焦于磨玻璃结节(GGN)或混合磨玻璃结节(mGGN)侵犯胸膜是否与实性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及预后一致,以及ⅠB期患者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合理分层问题。结合现有研究和临床实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胸膜侵犯的临床意义与分期争议
1. 胸膜侵犯的分期依据
根据第7版TNM分期,肿瘤侵犯脏层胸膜被定义为T2,对应ⅠB期(T2aN0M0)。但第8版分期中,T分期的标准更强调肿瘤大小和侵袭范围,而对胸膜侵犯的权重未单独调整。
关键争议点:胸膜侵犯是否应与其他T2特征(如肿瘤3-5cm、累及主支气管等)等同看待?
GGN的特殊性:GGN/mGGN多为惰性生长,病理类型常为原位腺癌(AIS)或微浸润腺癌(MIA),其胸膜侵犯可能仅反映局部黏连,而非侵袭性播散。
叶建明的想法:此问题AI的理解有误,其实若是原位癌或微浸润性腺癌,那是不可能侵犯胸膜的,侵犯胸膜就分到浸润性腺癌了。所以它分析了反映局部胸膜粘连而非侵袭性播散,只是从影像上挨胸膜近,判断为侵犯其实事实并不是侵犯。但我不是这意思,我问的是已经病理确定1B期的,侵犯胸膜的肺癌。当然其分析侵犯胸膜的权重是否等同于3-5厘米实性,累及主支气管等,当然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何况侵犯胸膜还有PL1与PL2呢?
2. 影像学与病理的差异
CT的局限性:胸膜牵拉征、分叶等影像特征对实性肿瘤更有提示意义,但对GGN/mGGN的胸膜侵犯判断不可靠,需依赖病理确诊。
C/T值的意义:若结节直径≤2cm且实性成分占比(C/T值)≤0.25,提示肿瘤侵袭性低,胸膜侵犯风险极低,即使CT显示“靠近胸膜”。
二、GGN/mGGN与实性肿瘤的恶性行为差异
1. 生物学行为对比
GGN/mGGN的惰性特征:以磨玻璃成分为主的肿瘤生长缓慢,转移风险显著低于实性肿瘤。例如,AIS和MIA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而实性肿瘤即使≤3cm也可能因微转移影响预后。
胸膜侵犯的预后影响:GGN/mGGN的胸膜侵犯可能仅代表局部黏连,而非广泛侵袭,其预后优于实性肿瘤伴胸膜侵犯。
2. 现有指南的局限性
数据来源偏倚:当前指南(如NCCN、CSCO)对ⅠB期的推荐基于历史研究,多数纳入患者为实性肿瘤,缺乏针对GGN/mGGN的亚组分析。
过度治疗风险:对于C/T值≤0.25、直径≤2cm的GGN/mGGN患者,若仅因胸膜侵犯即按指南推荐进行辅助治疗,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药物暴露和副作用。
叶建明的想法:上面AI给的意见正是我前面表达的意思:当时纳入的研究多数是实性肿瘤,缺乏对磨玻璃肺癌的亚组分析,而且估计很少病例是磨玻璃结节的,甚至是不是有都不一定。但却用从实性病灶得出的结果套用在近的大最检出的磨玻璃肺癌上,显然并不合理。
三、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分层策略建议
1.细化高危因素评估
推荐分层指标:
肿瘤大小与C/T值:≤2cm且C/T值≤0.25的GGN/mGGN,胸膜侵犯风险低,可豁免辅助治疗;
病理亚型:AIS/MIA无需辅助治疗,浸润性腺癌(IAC)需结合其他高危因素;
分子特征:EGFR突变阳性患者可能获益,但需权衡肿瘤侵袭性。
2. 个体化治疗决策
低危患者:符合C/T值低、无其他高危特征(如脉管侵犯、分化差)的ⅠB期患者,可仅观察随访;
高危患者:若合并肿瘤≥4cm、分化差或EGFR敏感突变,可考虑辅助靶向治疗。
四、叶建明观点的合理性及临床意义
叶建明教授强调“需根据GGN/mGGN的生物学特性细化分层”,这一观点更符合临床实际:
1.避免“一刀切”治疗:单纯因胸膜侵犯将GGN/mGGN与实性肿瘤等同处理,可能忽略其惰性本质,导致过度治疗;
2. 推动研究数据更新:呼吁针对GGN/mGGN开展前瞻性研究,明确胸膜侵犯对预后的独立影响,为指南更新提供依据。
总结
胸膜侵犯的临床意义需结合病理亚型和影像特征,不能简单等同于实性肿瘤的T2特征;
当前指南对ⅠB期的推荐需谨慎应用于GGN/mGGN患者,应通过C/T值、病理亚型等细化分层;
未来研究方向:建立基于GGN/mGGN特性的分期系统,优化辅助治疗适应症。
叶建明的观点反映了对现有指南局限性的批判性思考,强调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这一思路在磨玻璃结节主导的肺癌诊疗时代尤为关键。
感悟:
从AI的分析中,其实也是认可叶建明的观点的,认为我的观点反映了对现有指南局限性的批判性思考,强调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仍回到了我之前提出的“真早期”与“伪早期”理论上,存在淋巴结转移的,或大于5厘米以上实性的肺癌,本身并非早期,即使影像学检查没有远处转移,事实存在血行微转移的概率很大,任何针对晚期肺癌治疗手段前移或更积极的干预确实可能获益。但对于1B期的因为存在真伪早期的不同,不进行细致分层的一刀切方式予以术后辅助治疗必会伤及那些“真早期”的病人群体。何部这研究与结论是从传统实性肺癌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而目前更为常见的,我所质疑的却是磨玻璃肺癌。在目前医学条件下,无法完全做了真伪早期的甄别,但应该进行相关的研究,从以下方面入手:病灶密度与实性占比、病灶亚型与高危因素有无、随访进展速度、年龄与是否多原发癌、MRD的应用等,从而尽可能准确的进行分层,避免“隐形而且合规的过度治疗”!


